他們把鳥類圖鑑遞給我看,指著書上的內容篤定地告訴我:「活著的鶴會飛走,睡著的鶴是單腳站立的,只有死掉的鶴才趴在地上。」
──林俊龍,《沙壇城.到遠方》
我第一次接觸馬華文學,應該是李永平老師的〈拉子婦〉。這篇小說看似在寫家庭,寫婆媳,卻又不然。「拉子嬸」是沙勞越華人稱呼當地達雅族人的用語,「我」的三叔為了愛情挑戰了整個宗族,將拉子嬸娶回家,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家族緊張。這是因為華人雖然移民到他鄉,但宗族與種族概念仍然是深植,他們被部分當地人敵視,也鄙視當地人。「拉子嬸」這個詞就是帶著輕蔑的意味。
李永平是這樣直戳華人優越主義的:「倘若我不喊拉子,而用另外一個好聽點、友善點的名詞代替它,中國人會感到很彆扭的。」作為家中的成員,「拉子嬸是無聲無息中活著」,這麼說也不準確,實際上是無聲無息地「挨著」。那個看似啟動了一段驚天動地愛情的三叔,最後把拉子婦和她為他生的子女送回部落的長屋,無愧無疚地尋找自己的新愛情。拉子嬸挨夠了,便無聲無息地離開了。
這是一篇「非華人優越主義」的作品,作為移民的華人,在異鄉仍帶著優越感,而不只是為了利益和安全所組構的文化向心力而已。李永平的安靜敘事狠狠地刺痛了我。
俊龍在來到東華的時候,我並不知道他的馬來西亞的背景。我是從課堂他的作品,漸漸了解他的世界,或者說,他想要建立的世界。待在花蓮那幾年裡,我感覺俊龍曾經遇過兩次寫作上的糾結:一是他的閱讀依然是以台灣出版為中心的邏輯,二是他對自己的中文表達曾經產生懷疑。
第一個問題源自於俊龍作為一個外國人(身分是所謂的「僑生」),台灣文壇的認肯機制又是文學獎,而獎項是有國籍限制的。作為一個年輕的作者,在寫作尚未有自己的「內核」的時候往外探求,觀察台灣經典或年輕一輩作品去形塑自己寫作的樣貌是很自然的事。只是這種台灣年輕作家的尋常經驗讓俊龍感到有些不安,究竟什麼是自己想要追求的寫作(無論是題材或是文字風格)?而自己的文字表現會不會太不「台灣」,因此不被此地的讀者(特別是專業讀者—評審)接受?這樣的猶疑和不安,不可避免地出現了。
剛好我的創作課堂,很強調跳脫中文創作圈的生態,在更廣闊的世界尋找跟自己寫作步調較為一致的方式,因此創作課我是以翻譯文學作為主要樣本。在那些對台下學生來說,都一樣陌生的文化描述裡,在那些帶著「翻譯氣息」的中文裡,俊龍漸漸放開了自己題材的選擇與想像。畢竟,我們都可能屬於一個次文學圈子,同時也在另一個文學國界裡被認為是陌生的。
一次討論作品的過程中,我建議俊龍不必去迎合台灣式的中文,用他自己習慣的中文(特別是寫作對話時),甚至是翻譯腔的中文,馬來語、英語混血的中文也無妨。我的想法是,俊龍的身分是他寫作上不可繞道的事實,那麼,不妨就讓這樣的事實,成為他的寫作形象。
這並不是新見解,而是既成的推論。李永平十九歲來到台灣(一九六六),張貴興十八歲(一九七四),黃錦樹則是二十一歲(一九八八),他們大約在大學對知識的渴望最強、語言卻已經很難完全修正的時候來到台灣。他們的小說都從自己的故鄉(而不是台北這個新世界)的風土、物種、人物寫起,文字也保留了一些異地(對台灣讀者來說)的氣息,成為自我風格的特色。這三位作家後來都留在了台灣,當然也有求學後回鄉繼續創作的。俊龍在畢業之前就因為家庭因素兩度休學回到檳城,口試後亦未再回到台灣。雖然未來尚未可知,但目前的俊龍顯然更接近於「短暫客居」台灣的馬華人作家,未來雖然很可能在台灣長期有出版作品,但精神故鄉仍在彼端。這或許是一種第二層次的「寓居他鄉」。
俊龍的祖輩是中國廣東普寧的潮州人,曾祖帶著爺爺南下南洋後定居檳城。曾祖曾是修錶匠,後來開始參與本地的政治活動,甚或當上了勞工黨支部的祕書。五一三事件(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爆發的大規模種族衝突,主要發生在馬來人與華人之間)後,勞工黨開始式微,就不再參與政治活動了。俊龍的父親成為菜販,但也是一個小村子的村長。這是那一代華人移民的生存模式,用「做生意」來奠定經濟基礎,以從政來扎根。
但俊龍這第一本書裡的敘事,裡頭「他者」的經驗已經和上一輩與上上一輩的馬華作家經驗有了差異,而這差異是漸變的。賭雨和那些村子裡的軼事還有著祖輩的影子,賭馬、足球已經是父輩的生活經驗了,而以電競做為發想的終篇,則是俊龍這輩的現在式。俊龍把這個現在式,和「沙壇城」這樣帶著宗教意味的標題並置,讓那個虛擬的世界,就像法事前築起的小小壇城,既是通往未知的管道,又是緣生緣滅的暫時性存在。對我來說,這就是俊龍有意或無意的處境隱喻。俊龍這輩回望文化資產時的自我詮釋,已然不再是「解經」,而是他們必須要築城的現世。但那個「城」是緣生緣滅的存在,只是掃掉了城之後夢是否還在、記憶是否還在、愛是否還在,或許是俊龍透過作品想跟我們說的。
我這樣的解讀,和俊龍的自我界定並不相同(讀者可以看他自己的後記),只是我作為一個俗世讀者的「說法」(梵文:Dharma-desana)之一而已。
在這本小說集裡,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沒有太多技巧、太多隱喻的〈第二片屋瓦〉。小說裡的「賭雨」讓我讀來著迷,那是南洋民族因為食物豐富而比荒涼的北方多的一份悠閒,也是氣候與地景的文化產出。「賭」是一種把人性挖掘至底的人類遊戲,賭到最後不只是下不下雨,還要進一步猜中第一滴雨會落在哪一排、哪一片屋瓦上。
這種不科學的賭法,讓賭更讓人沉迷,因為結果不只是經驗、運氣,可能還包括權力以及命定的疏漏。賭贏了與賭輸了,或許在這樣的小鎮裡,最終的命運並沒有什麼不同,但在「那一刻」是不同的、生機勃勃的。這篇小說也彰顯了俊龍寫作的天性與風格,他的作品文藝腔低、敘事平順,卻常常在某些暫停的段落,發出令人沉思的喟嘆。
俊龍曾經在信裡告訴我,他未來有兩個長篇小說的計劃,一是近年的(寫檳城),另一個是十年內會寫的(西域之路)。我因為參加喬治市文學節(George Town Literary Festival, GTLF),和多年未見的俊龍和詩人周天派在檳城相遇。俊龍帶來當地傳統的豆沙餅,天派則陪我走逛海邊的船屋,我們短暫地聊了文學。我在想,對文學創作者來說,任何一個故鄉都像是要永世存在的繁複「沙壇城」,他們會用筆緊緊抓住城的每一個細節、每一段故事,盡全力用「根」來保持著城的「不散」。
我用「漸變」的角度來看俊龍這本初試啼聲的小說集,正因為他告訴我的這兩個寫作計畫,因為這意味著,他正在思考的是城的現世、前世與未來。
他是活著的鶴,「活著的鶴會飛走」,但會留下牠們睡著時單腳站立的腳印,我希望您能打開書頁,端詳這個新鮮的、還未石化的,也還沒有被潮水收走的腳印。
作者簡介
有時寫作、畫圖、攝影、耕作。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。
著有散文集《迷蝶誌》、《蝶道》、《家離水邊那麼近》、《浮光》;短篇小說集《本日公休》、《虎爺》、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,長篇小說《睡眠的航線》、《複眼人》、《單車失竊記》、《苦雨之地》、《海風酒店》,論文「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」三冊。
作品已譯為二十多國語言,曾獲法國島嶼文學獎小說獎(Prix du Livre Insulaire)、日本本屋大賞翻譯類第三名。並曾入圍(選)英國曼布克國際獎(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)、法國愛彌爾.吉美亞洲文學獎( Prix Émile Guimet de littérature asiatique )、德國柏林影展Books at Berlinale(Berlinale -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)、日本星雲獎(Seiun Awards Nominees)海外長編部門候補、《Time Out Beijing》百年來最佳中文小說、《亞洲週刊》年度十大中文小說、香港浸會大學紅樓夢專家推薦獎。
國內曾獲臺北國際書展小說大獎、臺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、《聯合報》文學大獎、金鼎獎年度最佳圖書、「開卷」年度好書及多項年度選書等。
延伸閱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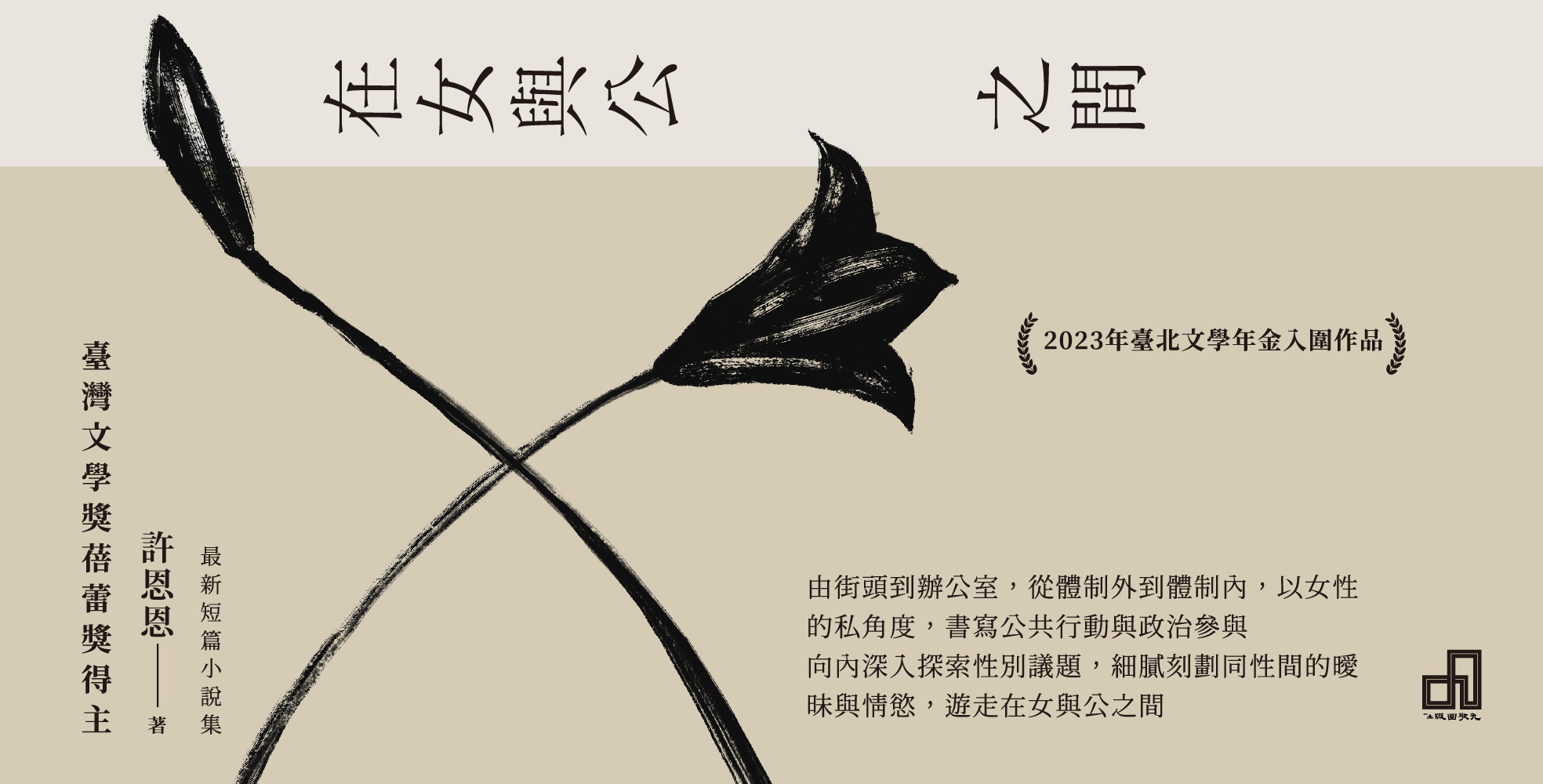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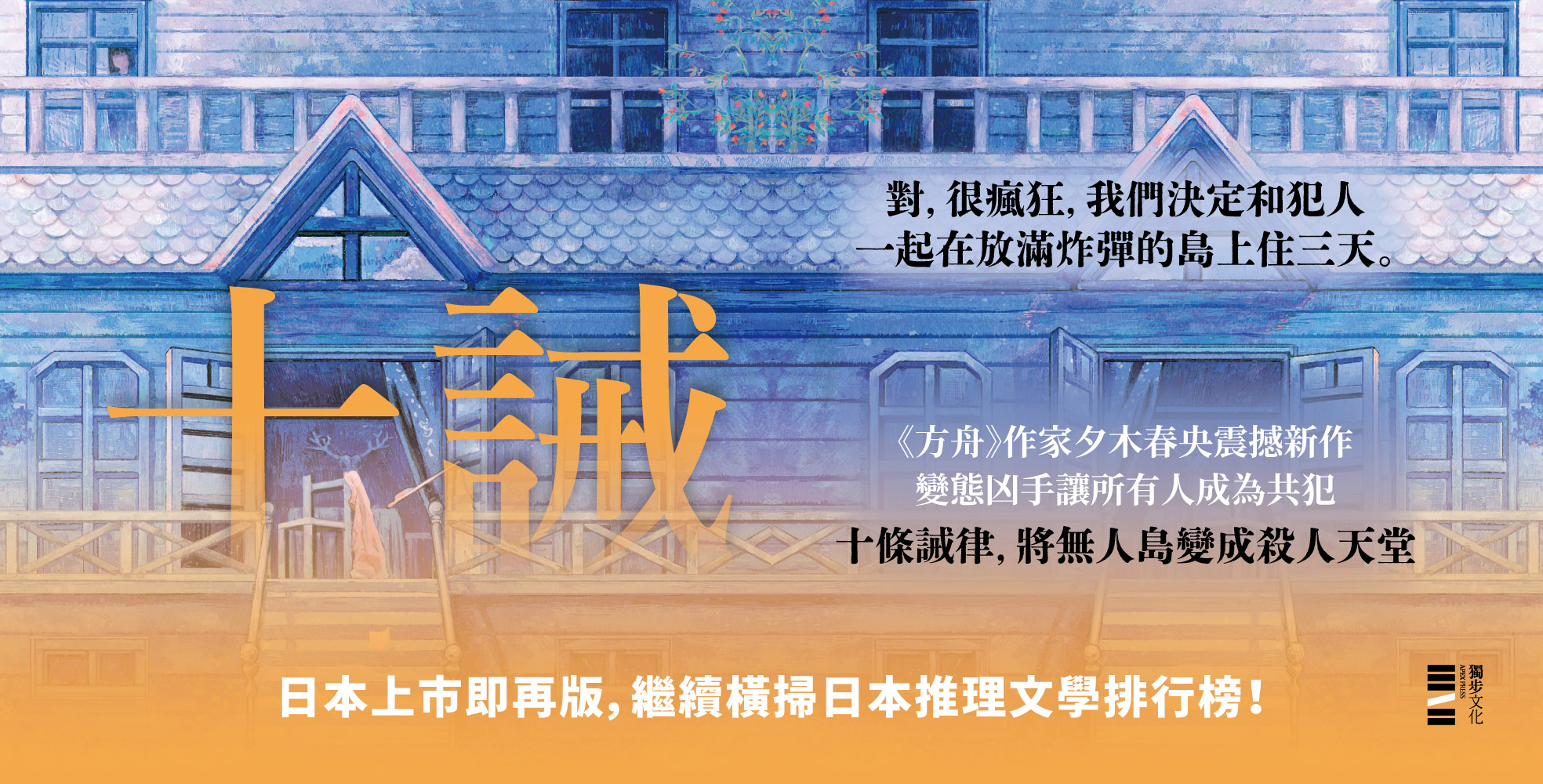








回文章列表